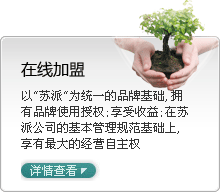企业故事

走进常州城
笔者:你是几岁开始学手艺的?
俞兆庆:十七岁。
笔者:哦,十七岁还是个孩子啊。
俞兆庆:是的。可是在父母的眼里,我已经是大人了,我得自己出去寻饭碗了,因为父母养不活我。
笔者:开始就学裁缝吗?
俞兆庆:开始是学的木匠,因为我的父亲是木匠。记得那一年的大伏天,正是水稻拔节的时候,可是天总是不下雨,靠天吃饭的农民只好到运河里去车水来灌溉水稻。富有的农民都可用牛来车水,穷苦的农民只好靠双脚车水。我十六岁就和父母亲、还有大哥站到了龙骨水车上,一脚一脚朝田里踩水。一天的水车下来,身上被烈日晒脱了皮,双脚踩出了血泡。今天的人很难体会到上个世纪的农民在龙骨水车上踩水的劳动强度,尤其是孩子跟着大人同在一架水车上劳动的残酷,水车轴上按着四个脚蹬,踩一圈,水车轴才能转一周,稍稍一慢,水车槽里的河水就会倒流。
傍晚,俞兆庆回到家,两条腿就不能动弹了,晚上睡觉,只好用双手将其搬上床。可是第二天天没亮,他又跟着父母亲、大哥上了水车,民以食为天,粮食就是农民的天啊,烈日似乎在跟这家人争夺着田里的水稻,一天不车水,水稻的叶子就会干瘪下去。上床可以自己搬脚,上龙骨水车却不能搬了,因为上了车两条胳膊必须趴在横梁上。娘不忍心双脚已经打出血泡的小儿子再上车踩水,可父亲却说,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气,水车出水就能多些,不能保住田里的水稻,就只能挨饿。父亲说,人是做不死的,却能饿死。为了不被饿死,俞兆庆只好咬着牙上车车水。干旱的夏季终于抗过去了,水稻保住了。可是人算不如天算,就在水稻灌浆之时,一场突然而至的稻瘟病,使田里的稻子全“白了头”。田地没有了收成,父亲只好扛起木匠工具出门打工。他是乡里闻名的一个好木匠,起房造屋,打床、做桌,木匠活样样精细,父亲站到一棵树下,一眼就能看出这棵树能派多大用场,大到能打一张床,还是一张桌子,小到几张板凳,凭眼光估算几乎是分毫不差,父亲在栗山禅寺雕塑的佛像曾倾倒了无数香客,还有他打的八仙桌成了江阴西乡的“名牌”,四乡八邻的人家都以拥有俞木匠打的一张八仙桌为荣,就像当今收藏了名家的字画一样荣耀。俞木匠打的木床,起码能睡三代人而不用修理,俞木匠造屋,房梁和柱子不用一颗钉子,他的木匠绝活就像一个神话,在江阴西乡经久不衰。
父亲背着木匠工具行走在西乡的大道上,那是一把斧子和一把锯子,锯绳上别着刨子、凿子、拉线盒等一系列工具,别看木匠这门手艺,它要懂几何学、力学、建筑学,还要懂美学、雕塑学,父亲背着工具走村窜户,大到起房造屋,小到做一张小凳,他样样都做,只要能挣到工钱养家糊口,旧时的工钱就是稻谷,做一天工,挣回几升稻谷,就算烧高香了,家里有四张嘴等着吃饭,父亲拚死拚活地做着,终于熬过了冬天,熬过了春荒。
春天万物复苏,是播种希望的季节,为了多收稻子,全家人又开始积肥。在水田一角,挖一个两丈见方的土塘,围上土堰,罱上河泥后,再将猪囤粪、青草之类堆到土塘里,进行捣肥,就是要将各种肥料搅拌在一起,进行发酵,这样的肥料在插秧前下到田里,肥力就足,要使肥料发酵好,就得搅拌均匀,搅拌得越匀,肥力就越足,有条件的农民,都是牵着水牛在草塘里转圈,水牛的四条腿就是四根有力的棍棒,能将草塘里的肥搅成浆糊状,可是俞家没有水牛,爹只好带着两个儿子用腿做搅棒,一天草塘踩下来,人都成了泥人,浑身散发着猪粪的气味,劳累是睡上一觉还能恢复,最难熬的是毛孔里钻满了细菌,痒得直钻心。如此残酷的劳动,16岁的俞兆庆都经历了。
他洒下汗水,本指望秋天能收获,可又是一场稻瘟病,将全家人的希望全化为乌有。
又是一个荒年来临了。俞兆庆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,这个念头起源于父亲的一句话,父亲的这句话也是从上代传下来的,这句话,曾经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,也改变了俞兆庆的命运。
父亲对我说过:“兆庆,荒年饿勿煞手艺人,你就学一门手艺吧,手艺人虽然苦,总可有口饭吃,能把自己的一张嘴度了”。起先,我是想学裁缝,因为我个头小,人又瘦,怕学别的手艺吃不消,可是父亲却让我学木匠,父亲说,裁缝不算匠,裁缝上门工,按照规矩东家是不供点心的,只能吃三顿饭,而木匠算匠,除了三顿饭,还有供点心吃。为了能多吃上一顿点心,我就学了木匠,那年月,人们把吃饭看得很重,碗里盛的饭菜,能代表一家人的身份、生活水平。能有点心吃,匠人的身份就要高一些。所谓三教九流,分得很清。再说父亲也希望我将来能接他的班,但父亲又不想直接带我,父亲非常爱我,不忍心打我,因为学手艺是要上规矩的,师傅是要打徒弟的,于是他就想把我送到常州去学木匠。
老木匠心里明白,父亲教不了儿子,因为木匠这门手艺太残酷了,他担心儿子跟着他就学不了,江阴有句俗话,学手艺得先吃三年萝卜干饭,还得吃师傅三年的戒尺。一条线画得不直,一块木料锯得不正,都得吃戒尺,可是做父亲的下不了这个手,他太疼爱这个儿子了,最要紧的是,儿子长得又瘦又小,站在那里比锯子高不了多少,学木匠是需要有一副好身板的,拉锯、伐树、造屋上梁都是力气活,可是儿子像个文弱书生,学不了木匠。但是让儿子呆在家里种田,就得饿死。
父亲想了两天,突然将儿子叫到跟前道:“兆庆,常州城里有个木匠铺,那里的师傅是我的师兄,你就去拜师学手艺吧。再说,学手艺就得学门像样的手艺,木匠是匠,裁缝不算匠,木匠上门工,东家都要供点心的,可是裁缝就说不上了。”俞兆庆点了点头,也许下午有供的一顿点心,对他产生了诱惑。17岁的儿子,似乎肚子就从来没有吃饱过一顿。
听说儿子要出门去学手艺,他娘一边抹着泪,一边为他准备行装和干粮。第二天一大早就给他煮了几个芋头婆,塞到他的怀里,娘关照儿子:从球庄到常州,要走三十多里的路,你走饿了,就从怀里拿出芋头婆来啃几口,芋头婆揣在怀里,有体温暖着,就不会凉。
父亲和娘送到村口,就站住了,父亲的口信早在前一天前就托人送到木匠铺了,父亲本想亲自送儿子过去,正好那天要上门工,就让儿子一人走了,儿子迟早要离开父母的,就让他一个人出去闯荡吧,那怕撞个头破血流,也能长一次记性。
俞兆庆上路了。走饿了,就吃芋头婆。走了好一会,终于走到了常州,找到了设在双桂坊的木匠铺。双桂坊是一个古巷,巷里店铺林立。在明朝曾出过两个状元,所以取双双折桂之意,因此而得名——双桂坊。大师傅正在朝一块木料上弹墨线,耳朵上架着一支竹片做的划线笔。看到有人站在门口,便看了他一眼,问道:“你就是俞木匠的儿子吧?”
“是。”俞兆庆点了点头。
“你晓得拜师的规矩吗?”大师傅又低头弹着墨线。
大师傅话音刚落,俞兆庆就扑通一声跪到大师傅面前,磕了三个头。
大师傅这才直起身子,一把将他扶起,看了面前的徒弟一眼,随后拿过一把大锯,竖到俞兆庆面前。大师傅让他扶住锯柄,把腰直起来,接连看了两眼,感叹道:“你都没有这把锯高,却还来学木匠!这个老俞木匠!”
“大师傅,我只要混口饭吃。”俞兆庆说。
“你当这口饭好吃吗?你晓得,常州城里有多少个木匠铺,光是西门,就有一条木匠街,那条街的木匠铺子做的马桶,足够供应全上海!好了,既然你都拜师了,我就得收下你,你就去干活吧。”大师傅说着,就让俞兆庆去拉锯。是用刚才跟他比身高的那把大锯锯一棵足有一人合围的大圆木。是两个人一起拉锯,那棵圆木斜竖着绑在三角架上,就叫俞兆庆站在圆木的一头,站在另一头的是师傅的大徒弟,两人你来我往地拉,锯着那棵圆木。

一上午拉下来,吃饭的时候,师傅叫做饭的老木匠将一碗干饭端到他面前,他的右手怎么也抓不住筷子了。他双手捧着饭碗转过身,他不想让大师傅看到他的可怜相,将沾满木屑的手按在裤腿上蹭了蹭,就用手抓起一把饭往嘴里塞去。他太饿了,那碗干饭上,撒了几块常州萝卜干,这是唯一的下饭菜,他一把接着一把将饭和萝卜干塞进嘴里,这是他有生以来吃得最饱的第一顿饭了。
他放下碗筷,已经吃完饭的师兄早就站到了大锯前。他们又接着拉起来。到天黑的时候,从锯齿流下的木屑已经在他面前堆了一大堆。
他接连拉了十多天大锯,拉到后来,他的两条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,夜里躺到床上,都不知道该朝哪里搁。
铺子里的大圆木都锯成了均匀的木板,下一步,就是将木板再锯成木条。听师兄说,大师傅正在给常州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打一张婚床,是给儿子结婚用的婚床,工艺要求极高,这剖板材的下手活,就交给了他,经过十多天的历练,大师傅发现,小徒弟很有悟性,是学木匠的料,当然最重要的是,他有文化。大师傅在每块木板上画了黑线,告诉小徒弟,这些板木,都是有限量的,锯坏了一块,是要赔给人家的,所以锯子口要跟着线走,不能走歪线,一旦锯出了次品,就得赔偿。
这下轮到他一个人拉锯了。木匠手工锯木,都作金鸡独立状,一只脚站在地上,一只脚踩住搁在板凳上的木板。锯了几天,他的两条胳膊都快要累断了,他走路都不敢大声喘气,生怕喘一口大气,整个身子骨就会散架。
三个多月后的一天夜里,当木匠铺打烊后,他一个人趴在灯下悄悄写了一封家信。他在信上说:“爸爸,我快要累死了,如果让我再在这里学下去,我真的要累死的。”